

自左向右:巴金、李辉、陈思和 资料图片

陈思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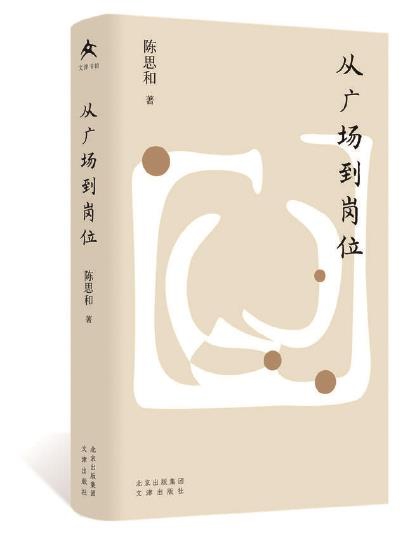
《从广场到岗位》陈思和 著
陈思和,1954年1月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主任,兼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当代文学批评等。曾当选2004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第三届国家名师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
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里的咖啡厅被命名为“星空”,“星空”下的办公室中的一间,属于陈思和教授的工作室。屋内一张长条桌,两侧靠墙,架子顶天立地,满满当当塞足书。在一层一层的书籍当中,一尊巴金先生的头像将来客的视线聚焦到这一列。此处藏有《家》《春》《秋》《寒夜》《憩园》《随想录》等巴金著作的各种版本,间隔以厚厚一沓《巴金研究论集》《巴金的世界》《巴金创作综论》等研究类著作……在它们中间,横放着一沓颜色淡黄的旧书。泛出褐色的书脊显示着其存世时间的久远。
陈思和教授走过去,拿起其中一本,展示给他的两位同事看。他们都是“90后”,是今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最新入职的两位青年教师,也都是陈思和的学生。
旧书的纸张散发着印刷品特有的气味,有些部分已经薄如蝉翼,那昆虫翅膀般的脉络,展露出岁月在字纸上留下的痕迹,如一个活物。陈思和像看到一位故交一样,亲切地翻动书页,指着书页的一处被精心补过的破损。
“你瞧,这是我亲手补的。”满头白发的陈思和把书展开递给两位青年,“如何补书的工艺我都会,因为我很早做过图书馆的工作。”
此时此刻,这个场景内,巴金、书籍、学生、补书,每一个要素,都是一个关键词,指向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文系教授、作家、文学批评家陈思和从教整整42年的历程。
42年前,28岁的陈思和毕业留校。师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贾植芳的他,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从巴金研究起步,进入以鲁迅为核心、以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为关怀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他提出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世界性因素、民间、潜在写作等研究方法与概念,始终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新世纪的首位系主任,陈思和努力把中文系下属二级学科推向全国一流水平,并支持王安忆在复旦成立全国首个MFA创意写作专业学位授权点;2014年至2022年,陈思和又担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今年秋天,陈思和教授从教42周年暨《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座谈会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院所的教师、作家、研究者齐聚一堂。热热闹闹的仪式结束,陈思和回到他的书架和书架之中。这个时刻,意味着陈思和从具体的在编岗位上退休,但他说,自己没有从育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更不会从学术研究的岗位上退下来。他希望,“在精神上仍要做真正的龙和虎”。
所以,与其说是“荣休”,他更看重从教42周年这个概念的意涵。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也曾在学生时代听过陈思和的课。他记得自己在陈思和老师《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上得了一个“良”。
在致辞中,裘新说:“思和老师始终保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古稀之年依然笔耕不辍。他的新书体现了他的学术集成与自我革新。”
该如何理解此处的“自我革新”?如何理解此处的新与旧?陈思和说,文学史的未来可以被创造,作者、读者、研究者等等,所有的文学工作者,都可能是未来文学史的创造者。如果把文学传统比作一条汹涌的精神之河,那么——
“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
在这条无边界的河流里,42年不过一瞬,《从广场到岗位》是一个锚点。以这块“水底的石头”为标志,陈思和要开启“中国现代文学史话语创新”系列写作,计划以六部作品“完成”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和人文学术的持续探索和发问。
一
周末周刊:光华楼下有一尊“驴背诗思”雕塑,让人联想到诗词中的许多文人形象。中国传统语汇中,似乎没有“知识分子”这一说,但一直有“士大夫”和“文人”的概念。如何理解您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
陈思和:岗位意识,是我在1993年知识界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时提出的。当时,面对市场化的冲击,人文精神出现的危机,大家都在思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知识分子如何保持和发扬原有的精神传统,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用了“岗位”这个概念,看中的是其“坚守”的意涵。
岗位与职业还是有区别的。我的理解,“岗位”包含三重意思:专业、职业、事业。专业为岗位的识别和基础;职业是专业服务于社会、实现其价值的中介;而事业联系着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成为一种人生成熟的标志。
1993年,我发表论文《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讨论了“庙堂型”“广场型”“岗位型”三种价值取向。
传统文人的价值取向是和“学而优则仕”的概念相联系的,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人最终的社会价值是要贡献给帝王。“终身布衣”在这个儒家文化语境下,除了士大夫有意识地在拒绝“摧眉折腰事权贵”时体现价值之外,一般是没有价值的。
晚清以后,现代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讲课、著述、出版、版税来养活自己,这就改变了以往完全依傍体制的生存形态,转型为一个新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独立知识分子形象。如张元济通过编写现代教科书来改造商务印书馆,严复以翻译稿费实现财务独立。以他们为例,我们能否探讨当下知识分子既能成功实现知识转换带来经济收入,又能保持安身立命的精神传统的可能性?
周末周刊:您曾说,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自信。这种自信不是“盲目投入社会大趋势随波逐流,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在集体狂欢中验证自我存在感”,也不是“用拒绝社会潮流的冷漠态度,愤世嫉俗,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您说,真正自信的人,“一定敢于无视或者藐视滔滔俗流,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专心致志地做好自己责任范围以内的事情”。
陈思和:知识分子应该对社会尽自己的责任。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是责任的代码。知识分子要“坚守岗位”,就是要在各类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同时,在谋生之外有超越岗位的自觉,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担当、有所贡献,现代社会才能朝着理想的方向不断自我完善。
现代社会由大量的工作岗位构成,每一个岗位又是通过具体的专业和职业来体现的。专业有自己的传统,职业有自己的行规和标准,这样就慢慢形成了各自并行不悖的知识体系。这种体系不是自上而下由国家法律制定的,而是由每个专业根据自己的运行逻辑生成的。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周末周刊:三十年过去,如今的我们对参与市场竞争不再感到陌生。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回头看“人文精神大讨论”时,如何再理解当下知识分子所担负的责任?
陈思和:现在,人们在被解放的巨大物质欲望支配下参与市场竞争,带来很强的自我消耗。如今的学生、青年教师面对的严峻竞争,是我年轻时当学生、当教师时没有遇到过的挑战。如果没有更高的精神理念支撑,人很容易陷入被淘汰的恐惧,变得焦虑不安。所以我要强调,人生的岗位除了专业、职业以外,还需要有更重要的精神价值取向支撑。
三十年过去,我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三十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并不过时。因为人始终在面对不同的挑战,人始终在害怕自身的毁灭,但同时人也会始终反思自身。知识分子所坚守的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争,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始终要去直面并不断克服自身的丑陋面——要把这个“人”字写端正。
二
周末周刊:“要把这个‘人’字写端正”正是您的老师贾植芳先生生前一直提到的一句话。您自己的父亲很早逝世,您曾多次提到,在您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寻找精神的支撑力,一直“特别向往有一个父亲这样的人带领我”,直到进入复旦大学,遇见贾植芳先生。
陈思和:在我心里,贾植芳先生是以个人人格魅力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交集于一体的典范。贾植芳教授延续了鲁迅、胡风这一脉五四新文学战斗的精神传统,并薪尽火传,身体力行,把更多的青年人带进现代文学的传统源流之中。如果没有进入复旦大学,没有遇到贾植芳先生,我大概完全会过另一种人生吧。
周末周刊:您是主动接受老师影响的吗?
陈思和:受影响这件事,其实当下是看不见也无法察觉的,但是很多年后回过头想一想,我就是被潜移默化成这样了。我们说,教育是春风化雨,“化”,就是看不出的。
贾植芳先生生于山西襄汾,他的伯父是个买办,经商致富后资助侄儿们读书。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伯父见他生活坎坷,曾劝他回家继承家业做个商人。贾植芳并不轻视经商,但他回答:“伯父,你出钱培养我读书,就是让我活得像个人样,有自己独立的追求。”贾植芳此后大半生闯荡在战场、文坛内外,还多次坐过监狱,直到晚年才安定下来。看上去,伯父为他选择的道路似乎更稳妥,但其实,贾先生的心中是有归宿的。有一样东西是从读书中获得的,比一般的建功立业更为重要、更有价值,这个东西就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
贾植芳先生去世后,我为他作挽联:“从胡风追鲁迅,横眉冷对热肠扶颠,聚傲骨良心悲智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进书房,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创作翻译育人开八面来风。”这是我和朋友们几经斟酌修改所定的。
我没有把先生一生坎坷多次入狱的事迹写入挽联。在降志辱身的监狱里保持矢志不渝的高风亮节,固然体现了知识分子在苦难中求索真理实践人格的高贵精神,但我更想突出先生在普通生活中辛勤劳作的价值,先生在知识分子岗位上对人文学术所做出的贡献,那种融入日常的教学劳动,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德行”。
周末周刊:还是回到寻常、回到岗位、回到日课上?
陈思和:对,在每一个寻常岗位的日常坚守中体现其光荣和尊严,支撑起一个人的职业空间,并在这个空间里多层次地展开自己的价值。陈寅恪写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寻找到这种追求真理的快乐,胜于世间一切名利。这本身就体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即,把发现真理作为价值的最高标准。
哪怕在看起来最不能做事情的时代里,仍然可以做一些事情。个人的立场首先是一种理性的选择,首先要有一个独立的批判的立场,并且有实践这个立场的自觉。
周末周刊:做事情的精神。
陈思和:中国人常说“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在我看来,“立德”表现为一个人能否为周围环境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通过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来影响他人,并有能力将这种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去。
贾先生的“德行”在于他感性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精神特征,并以此来贯彻人生,影响他人,这便是在“立德”;以五四精神传统来教书育人,传递薪火,便在“立功”;至于“立言”,在我看来,只是“德”与“功”的注释,不是第一位的。先生在复旦大学原创性地建设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点,培养并影响了一大批学术梯队,这比著书立传本身更有价值。
三
周末周刊:在这次从教42周年暨《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座谈会上,您也没有把著书立说放在第一位,您说您自己“第一职业是教育,业余爱好才是写作。某种意义上,学生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陈思和:是的。我很看重。我的大部分学生接受教育以后,都在三尺讲台。像复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就是我任班主任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今年我的学生里也有年轻人留校任教,他们已经是90后的一代。还有更多的学生毕业以后,把在复旦学到的文化知识和精神传统传播到全国各地,培养出更多优秀年轻人。
一个人回头看时,才会惊觉时间过得多快。我去复旦大学报到时的场景,仿佛也就是不久之前的事。那时,我衣袋里放着录取通知书,因为心情激动,没留神提前下了公交车,多走了半站路才到校门。五六分钟的路程,好像走了很久很久。但回望42年,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
对我来说,年轻时有幸跟着贾植芳先生学习,追随他的道路成为教师,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我曾听先生说过,他在上世纪50年代总是在夜里准备第二天的讲课内容,一般都不睡觉,直到第二天白天上完课了才回家睡觉。他的精彩的课堂讲授完全是建立在彻夜不眠的精心准备之上的。
贾植芳先生的教育观完全是有教无类的,只要有青年人登门造访,无论亲疏,也无论是为了个人目的求教求助,还是为了人生学问中的大疑惑,他都一视同仁,竭力相助,热情对待。对我来说,追随在老师身边,耳濡目染,当然会觉得当老师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
周末周刊:您现在还担任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主任,这个工作主要负责什么?
陈思和:主要是对“评价”进行评价,如对学术与教育评价、科技与科创评价、社会与治理评价等全社会要素评价和智能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为国家数字化智能社会转型做好综合性服务。
周末周刊:现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会主动向您反映他们生活中的压力、学术研究的压力吗?
陈思和:当然有很强烈的反映,这种压力大家都感受得到。我自己作为过来人,当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压力。当时学校虽然也有很多困难,不过还是很重视为青年教师提供创造发展的空间。当时有“打擂台”的制度,把青年学者与中年学者评审职称的系列分开。后来又有“代表作”制度,灵活地处理教师升等的标准等等。
我觉得高校需要有评价体系,但目的是使评价体系更好地激活青年学者的思想能力和创作力,而不是框死他们的学术活力,扼杀他们的创造性。这值得更多人的关注。
我现在花比较多的时间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如何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标准,全面考核青年教师的能力,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学术环境。评价是为了提升青年教师、青年学者安身立命的自觉和自信,而不能导致青年教师没有安全感。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在具体而微的工作岗位中自觉担当,薪火相传。我们要给予青年一代更多的实践空间。
四
周末周刊:今年11月25日是文学巨匠巴金先生120周年诞辰。当年在贾植芳先生的指导下,您将巴金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起点。说说您第一次见到巴金时的场景好吗?
陈思和:1978年下半年起,我与同学李辉一起通读《巴金文集》,后来开始跟随贾植芳先生做研究。我们的第一篇文章《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以书简形式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六年后,我与李辉合作的第一本论文集《巴金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在现实生活里谒见巴金先生,是在1982年1月7日,这是后来李辉翻他的日记和我确认的时间。那时候我和李辉面临毕业,他被分到北京工作,马上要离开上海了,临走前想见一次巴金。在我们同班同学李小棠兄的安排下,我俩才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巴金先生的家。
我已经记不起当时和巴金先生具体说了什么。那时我和李辉有分工,我们与一些文化老人作访谈,都是我负责提问,他负责记录。所以李辉那里都有详细的笔记。只记得巴金先生穿了一件中山装,下楼时脚步沉重。那天他身体不好,有些发烧,我们谈话到一半,有人进来为他注射针药,巴金先生起身,然后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当他走出客厅时,我和李辉对视一下,非常惶恐。因为拜访是事先约好的,我们不知道巴金先生身体不舒服,我俩觉得自己怎么能这样惊扰大师。但巴金先生打好针又进来与我们继续说话,非常随和。
我和李辉跟随贾植芳开始研究巴金的1978年底,当时74岁的巴金正在香港《大公报》上开始发表《随想录》。这本书是作家解剖心灵的自白书。巴金反复强调“讲真话”,敢于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思考。正如萧乾说的,“巴金的伟大之处在于敢否定自己”,我觉得,在巴金身上,体现了“五四运动”的青年精神,始终追求真理。巴金先生活了一百多岁,仍然是个年轻人。
在我跟随贾植芳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初期,先生着重要求我做到两点:一是从寻找真相出发,尊重历史真实。二是要多学几门外语,要从世界的范围来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成果。贾植芳先生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巴金专集》时,主动把眼光放到国外的研究著作,从中来深入了解巴金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当时我和李辉还在念本科,先生就交给我们一本美国学者奥尔格·朗的研究专著,要我们从中翻译有关章节编入专集。我们之所以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与这本书直接有关,我们从这部研究著作中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巴金文学世界。
巴金先生的作品,现在看来,仍有一种天真和单纯,他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直到人生暮年都没有失去的理想和热情。我想,巴金先生永远不会过时。如鲁迅先生所言:“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回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巴金是在电视里看到他在挨批斗。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是被打上负面标签的,这反而引起我的好奇心,开始到处寻找巴金的作品来阅读。后来进入复旦大学,开始研究巴金,熟悉巴金。他不是一个擅长讲话的长者,我们去见他,要自己准备好多问题,我们问什么他就回答。但他自己在文章里一直讲,他很珍惜和青年人交流的机会。
对我来说,很幸运能和巴金这样亲历五四一代的作家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被他的作品感动、被他的人格感动,对他一直怀着很崇敬的心理。巴金不仅是一个文学家的巴金,更是思想者的巴金。武康路113号不仅是巴老居住的地方,更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周末周刊:你说过,如果把文学传统比作一条汹涌的精神之河,那么,“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
陈思和:每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追求,都不是孤立的“代”的努力追求,彼此之间是有传承和回响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前赴后继的关系。历史研究与当下研究必须联系在一起,当下必然伸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