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前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87-2001)、复旦大学校长(1993-1999)、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2001-2012),是享誉世界的中国当代著名核物理学家和教育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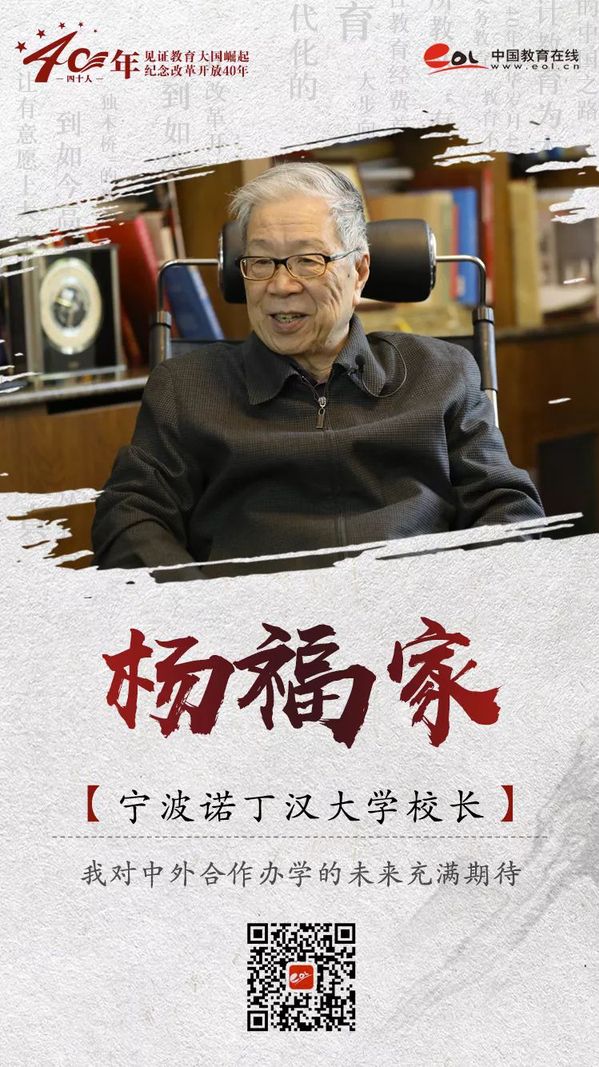
扫码查看专题

父辈的教导,要念书、要诚实
陈志文:您上世纪50年代进入复旦大学,那时候能上大学的人非常少。我们了解到,您的家乡宁波镇海走出过30位两院院士。您的家庭里也出了您和您三哥杨福愉两位院士,这是否与您的家庭教育有一些关系?
杨福家:我一共有八个兄弟姐妹,大哥过世得早,我没有见过,我是最小的。我父亲做生意,开始时家里比较宽裕,他过世后,家里就比较艰难了。但他严令下来一句话,再穷也要尽一切力量让我们念书。
陈志文:这很重要,一般家庭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要解决孩子的生存问题。
杨福家:父亲的两个教育理念让我印象深刻,第一是要念书,第二是要诚实,再穷也不能欺骗。这也是家庭对我最重要的两个影响。但其实,一个人的成长是要靠机遇的,不是自己或者家庭能完全决定。
我初中的时候很调皮,有一次把一根粉笔放在了黑板擦里,老师擦黑板时就越擦越脏。问是谁干的,我举手说是我干的。因为这件事,我被学校退学了,后来又辗转了几所学校。之后我很幸运考到了格致中学,格致中学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刚去的时候,成绩不是太好。有一次,老师组织我们念了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段话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段话引导了我思考,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该干什么?是要努力奋斗。

所谓学问,就是学习问问题
陈志文:当初上大学时,您为什么会选择物理?
杨福家:在中学时,我就觉得物理很有趣。考大学时,人家说物理系不好考,但我兴趣在这里,就想试试看,最终考上了。格致中学给了我足够的基础。
陈志文:您当时最心仪哪一所大学?
杨福家:北大比较有名,但人家劝我北大太难考了,家里人也不太赞成,觉得我还是在上海比较好。最后我还是留在了上海。实际上复旦大学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改变了我对很多东西的认识。
复旦大学本来是没有名气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很多有名的教师全都过来了。在复旦我意识到,在大学里上大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小班课。当时复旦的小班课是习题课,由助教来带,给同学们解答问题,同时也出一些习题给同学们做。

杨福家 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复旦大学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福家:复旦给了我很牢固的基础。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比如,一年级讲普通物理学的王福山教授,二年级的周同庆教授,讲数学物理方法的王恒守教授,还有卢鹤绂教授等。
卢先生对我的一生影响也很大。四年级的时候他给我们上课,鼓励大家提问题,启发我们独立思考。有一次上课时,我提出来他一个公式写的不太妥当,他说回去再查一下。后来,他请我到他家里说,你讲的是对的,下次上课我会纠正,一点儿都没生气。这就是大师风范。
他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给我出的题目非常难,最后我没有做出来。后来其他科学家做出来了,而且拿了奖。但卢先生说,做了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陈志文:您怎么评价复旦?您觉得复旦大学的特质是什么?
杨福家:第一,复旦的老师特别好,讲课讲的非常精彩。如上所述,院系调整后,复旦来了许多杰出教师。带我们习题课的助教们也非常好,好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教授。
第二,复旦的治学精神非常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复旦大学的校训。我最欣赏的是每一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博学的学,切问的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答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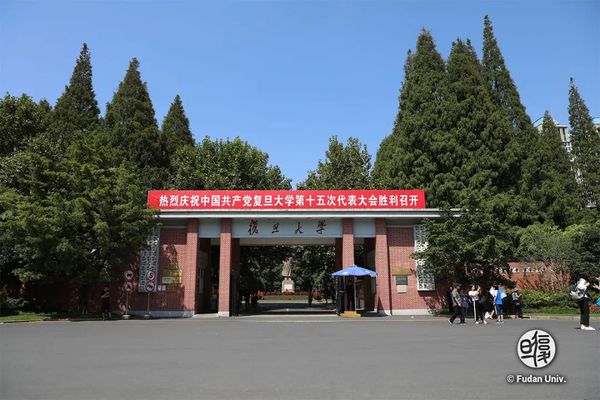
图源:复旦大学官博
陈志文:其实,只有学习过、思考过才会有问题。这与我们过去注重知识传授是很不一样的。
您有一段很特殊的出国经历。1963年您去丹麦访学,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少有的,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杨福家:这要感谢邓小平。建国后,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派往苏联,我哥哥就是在苏联拿的博士学位。在中苏关系破裂后,邓小平同志就讲了一句话“往西方派”。现在听起来很自然,但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我被选拔为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候选人,集中到北京进行英语培训。一开始许国璋考我们英语,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他说,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英语考试,不要说半年,两年能通过就不错了。后来我同来自北京大学的陈佳洱讲,我们的英文不见得就像他说的那么差,我俩约定从第二天起就只讲英文,不讲中文。最后,我们两个都通过了,我去了丹麦,他去了英国。这个机会应该说是邓小平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陈志文:在丹麦的两年里,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杨福家: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所以经常连夜做实验。玻尔实验室的分工很明确。有一次我要熬夜做实验,担心仪器坏了没办法修。管仪器的同事就给我准备了6台。
我在丹麦玻尔实验室的第一年主要是与丹麦人Per Rex Christensen合作,做出了很多成果,得到了玻尔教授的认可,邀请我又延长了一年在丹麦的时间。玻尔教授也非常鼓励我们提问。
第二年有位美国科学家提出想加入我们。我报告给了大使馆,大使馆同意了。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放弃了在合作成果上署名,那位美国科学家非常感动,他觉得主要工作是我做的。这件事也为我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任职于美国武器研究院,后来主动向我发出了访问邀请,促成了中国代表团对美国武器研究院的两次访问。
1983年的那一次,氢弹之父于敏也去了,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国。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他们有60个人陪同。美国武器研究所里有一个基础研究部。我一开始很奇怪,做基础研究的人又不搞武器,为什么要请他们。后来了解到,在基础研究部的科学家可以搞自己的基础研究,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讨论武器时得听着。这也就是美国武器研究所的高明之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提出来的意见,搞武器的人是提不出来的,这些意见能从根本上提高武器的性能。
陈志文:这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理工结合。没有很好的理科,就很难有好的工科。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特色办学之路
陈志文:您是解放后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担任英国皇家特许大学校长的中国人。能否给我讲述一下其中的一些故事?
杨福家:1999年我辞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后,香港大学和英国诺丁汉大学分别授予了我名誉博士学位。我当时没有想到,在2000年底,英国诺丁汉大学邀请我做校长。经过协商洽谈,我接任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一职。
陈志文:在2004年,您又创造了一个第一,推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初衷是什么?
杨福家:说来也巧,我在英国当校长,在为英国服务的同时,也想为中国服务。恰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于2003年颁布了,从法律的层面为中外合作大学的举办创造了环境。万里集团的董事长徐亚芬也在这时候找到了我,我们一拍即合,开始筹办宁波诺丁汉大学。

来源:宁波诺丁汉大学官博
陈志文: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学生培养上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杨福家:宁波诺丁汉大学将英国的一些方式方法移植了过来。比如采取“小班化”教学,每个班只有15个同学,一个都不能多,老师讲5到10分钟,接下来是学生讨论。老师并不在意学生的答案,而是看学生的思路对不对,然后给学生很多参考书目,让他们自己去读。
陈志文:当时,宁波诺丁汉大学是想在国内建立一所以英国教育方式为主的高等学校,是吗?
杨福家:对,但我们有更多的创造性。即便是英国也没完全做到“小班化教学”,我们做到了。
当然这种办学模式一开始也有阻力,学生家长有很多意见,认为宁诺的学费比其他学校高那么多,怎么不上课,讨论讨论就结束了。后来,他们慢慢认识到了这种方式的好处,引导学生问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陈志文:在创办初期,您能想到十几年后,宁波诺丁汉大学成为了一所口碑这么好的学校吗?
杨福家:应该说是没有想到。但话说回来,能办成这样是必然的。一方面学生们很珍惜这个机会;另一方面学校引导学生去独立思考,自觉地去找知识,懂得了提问题的重要性。
陈志文:您怎么评价宁波诺丁汉大学?特点是什么?
杨福家:评价一所大学好不好,要看进来的学生和出去的学生。进来的学生越来越好,学校越来越难考,出去的学生也就越来越好。什么叫好?要么是去非常好的大学深造,要么是去非常好的企业工作。我看到2015年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生去向表,特别好,就送到了刘延东副总理那里。后来她跟我讲,你们学校确实与众不同,培养的人都很优秀。
陈志文:您对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意见?
杨福家:现在中外合作大学越来越多了,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等。层次越来越高,办的越来越好,对此,我是充满期待的。

本科教育是重塑学生价值观的关键
陈志文:您怎么看待本科教育对于学生的影响?
杨福家:在本科阶段,学生的人生观还没有形成。因此,大学对他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是再次塑造的过程。本科教育最主要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平衡发展,使学生具备开放而全面的视野,以及均衡发展的人格,做人第一、学问第二。
陈志文:您在复旦时曾颁布了一项措施,对学生作弊的行为实施退学。坦率地讲,对于此事社会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当时您顶着压力做这件事是基于什么考虑?
杨福家:如果一所学校不能抵制作弊风,是不可能办好的。在第一批退学的学生里有一位来自我母校格致中学的毕业生。我当时很痛心,但一样开除了。后来,我与格致中学的校长讲了这事,他完全同意。
陈志文:作弊在英美高校是严令禁止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做人问题。
杨福家:是的。

杨福家(右) 陈志文(左)中国教育在线/摄
陈志文:现在中国高校长期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您怎么看?
杨福家:从我开始做校长时就认为,教授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把教学搞好,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科学研究。教学是教授的本职工作,科学研究是教授自己要做的事情。我相信,有能力的人,一定可以两者兼顾。如果不搞研究,就没有更多新的东西,教学也是教不好的。一流的教授,一定是教学科研并重的。
陈志文:您的专业是物理,但您也特别强调人文修养,为什么?
杨福家:因为慢慢地,我觉得人文和科技是分不开的,是密切相关的。

高等教育要鼓励各类型院校共同发展
陈志文:您觉得中国高等教育这几十年发展得怎么样?
杨福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社会培养了很多人才,从这个方面讲,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是巨大的。现在各行各业第一线的人,基本上都是中国大学培养的。
陈志文:您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还有怎样的建议?
杨福家:一是,我觉得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对不同类型的高校(研究型大学、一般性大学、职业高校)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要鼓励各类高等院校的发展。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我提出来它的定位是一般性大学,而不是研究型大学,定位清晰了,事情就好做了。
此外,现在社会上对职业教育还有偏见,认为只有能力差、不好管教的人才上职业院校,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尊重职业教育,尊重孩子们的职业发展规划。我在美国的侄女,她的女儿成绩优异,可以上名校,但她遵循自己的意愿读了烹饪学校,专做艺术蛋糕,最终也实现了人生理想和价值。所以,高等教育应该鼓励多元评价体系,消除区别待遇。
二是,我觉得国内的校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是非常不妥当的。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做了十二年校长,而中国校长一般是最多做两届。校长可以一直做下去,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思考。不同校长有不同的治校理念,如果校长换的比较频繁,学校发展的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
陈志文:也就是说,您觉得校长还是要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里,对学校进行治理。
杨福家:只有做校长的时间长了,他才有底气。现在我们很多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的。我完全赞成给他们副部级待遇,但不能当作副部级管理。
陈志文:您曾担任过中外三所高校的校长,复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给您带来的不同感受是什么?
杨福家: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如何对待学生的。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当校长时,唯一不能请假的事情是毕业典礼。英国诺丁汉大学毕业典礼要开9天,宁波诺丁汉大学每年有六场毕业典礼。对我来讲,是很累。但对学生们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很惭愧,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没有做到。
陈志文:现在英国很多学校对于学位证书的授予都很隆重,仪式、着装等要求都很严格。
杨福家:对,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最珍贵的校长袍,还有学校里唯一一顶金边帽子。我一定要亲自为每一位学生颁发证书,并送上祝福。
陈志文:最后,如果让您对自己做一个总结,您觉得自己的特点是什么?
杨福家:追求卓越,这是我的人生追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追求卓越》。我认为,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中国教育在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