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江山图》全文未出现过“爱情”二字,读者看到最后,只看到为千里江山奋不顾身的年轻人。文艺批评家毛尖感慨,“这真是孙甘露写得最好的一封情书。他不仅自己版本升级了,也让这个时代的爱情版本升级了。”2023年,先锋小说家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斩获茅盾文学奖,成为继王安忆、金宇澄之后,第三位获得该奖的上海作家。
4月23日下午,孙甘露在“阅读上海”复旦大学第十二届读书节上亮相,作“文学中的上海”主旨演讲。同日下午,根据小说《千里江山图》改编、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张瑞涵、马伊琍、韩秀一、冯晖、杜若溪等主演的话剧在复旦相辉堂上演,北堂座无虚席。
“写小说好比‘纸上谈兵’。要把它演出来需要真实鲜活的人,有心跳、有血压、有气息。书是一种媒介、以文字为载体,而在剧场里观众看到的、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我曾看过这部话剧的首演,演得很好。”孙甘露在接受复旦大学融媒体记者采访时说。

对话复旦师生,讲述文学与人生
《千里江山图》围绕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和一个即将启动的名为“千里江山图”的秘密行动而展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以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为背景,融入革命、谍战、理想、情感等元素,描摹出英勇无畏的共产党人群像,记录了陈千里等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千里江山图》涉及的历史是来自个人想象还是史实考察?孙甘露坦言,作家写作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本书是涉及到中共党史的历史题材,在材料的考据上慎之又慎。“不过小说创作不是一个材料的竞赛,它兼有想象和历史材料。有时候想象所抵达的真实,比材料更加真实。”
孙甘露认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空间,他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重大的历史事实方面避免虚构、尊重史实,而在小细节上适当地虚构,进行一些文学创作,为此,他做了很多的采访和资料准备。小说前后写作历时一年多。但实际可能准备的时间更长。
“还原当地具体的某一天、某一时刻,以及其中的人物和当时做的事、看到的东西、吃的东西、心里的感受,以及面对一些具体时刻的时候,他究竟是怎么做抉择的。这些对我们后人来说,很值得深思,很想去一探究竟。”另一方面,写作在具体时间有具体的愿望,比如青年时期有较多幻想、不受拘束,中年以后转向对于历史的观照。

坐在孙甘露身边的,是复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王宏图。他和孙甘露是多年老友,曾第一时间参加了《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孙老师80年代创作了很有‘先锋特色’的小说,对照《千里江山图》和早期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在某些程度上,早期的作品更多像诗,就像带有非常强烈的梦幻色彩的诗;《千里江山图》是红色作品,同时又是一部叙事作品。”

讲座尾声,孙甘露与复旦师生交流。一位图书馆硕士研究生阅读《千里江山图》时被荡气回肠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向孙甘露提问:“您觉得话剧语言的呈现或者影视的表达方式,与小说语言有什么样的区别?”孙甘露认为,不同的艺术形式各擅胜场。《千里江山图》已被改编为话剧、评弹、广播剧、剧本杀等艺术形式,还将被改编为电视剧、电影等。孙甘露没有参与任何一个版本的改编,因为他想交给专业的人们去做。

相辉堂。伴随着话剧《千里江山图》大幕拉开,复旦师生仿佛重回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沉浸式感受那些隐姓埋名、在黑暗中点燃火炬的英雄故事。话剧采用叙事体的形式,舞台上,一群阅读小说的当代青年渐渐化为书中人物,并不断在两者间穿梭。演员用生动的表演力,充盈而磅礴的情感逐渐将剧情推向高潮,更让原著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为了在舞台上实现小说中“移步换景”式的叙事转场,话剧《千里江山图》利用虚实结合,同时通过装置组合与转台设计,为场景的切换和舞台动线提供更多灵活性。
“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话剧结尾,演员们在星空背景中交替朗诵原著小说中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这个关于理想、关于信仰、关于牺牲的故事让师生泪目,相辉堂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话剧《千里江山图》的改编基本忠实于原著,采用了国际流行的‘边说边演’的方式,团队付出了心血,整体的舞台呈现、场面调度、表演音乐都令人感动。”孙甘露在采访中对话剧的编剧和导演表达感谢,赞赏演员的演出。同时他认为话剧虽然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却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作品了。
一位MFA创意写作专业的女同学向孙老师请教“如何提升写作者的自觉或自信”,孙甘露回答:“写作是创造,小说写作是一个想象性的活动,最重要的还是感受一个人。写作是伴随着你的成长而来的,我觉得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时间点。写作对你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就是你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孙甘露: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上海记忆
活动开始前,孙甘露老师接受学校专访,讲述《千里江山图》的背后故事,分享创作与阅读的心得感悟。
1933年,茅盾在上海出版了长篇小说《子夜》,而《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也发生在那一年的上海。90年后,2023年8月11日,孙甘露以《千里江山图》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上海这座城市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纽带,交织时空的回响。
作为继王安忆、金宇澄之后第三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作家,孙甘露坦言:“上海毫无疑问是上海作家最重要的一个描写对象,因为我们就生活在其中。”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某种意义上,上海对我们来说就是全世界。
外滩华懋饭店、世界大旅社、邮政大楼、大光明大戏院、肇嘉浜、朱家角镇……孙甘露在《千里江山图》中勾勒出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城市记忆,来源于自身生活经验、档案资料考察与历史专家采访等方面。“我出生在上海,在上海生活了60多年,这些经历、经验和记忆慢慢地心里产生各种化学反应。书里写到的这些地点,对我来说是很多年里每天路过的地方,非常熟悉。”

《千里江山图》拥有一个真实而宏大的历史背景,“但是这个故事从‘千里江山图’的书名,一直到最后的附录都是虚构的。”曾经有读者看到全书最后《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以及附录的口述记录、牺牲烈士名单等材料,为“真实”的描写而感动落泪。孙甘露则说:“小说正文后的附录都是虚构的,把它放在小说正文的最后,也是小说写作的一部分。”而在小说正文紧迫的任务后面放进来一封抒情的书信,“读者可以发挥想象力,看成是书中具体人物写给另一个人的书信,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所有人写给所有人,或者当时的人献给今天的人的一封信。”
爱情,是孙甘露的主要发明。但是,十八万字的《千里江山图》,没有出现过“爱情”两个字。虽然小说中也有几对青年男女,但孙甘露没有给他们时间谈情说爱。“文学创作也是营造真实性,给读者营造真实感是一个蛮重要的方面。因为《千里江山图》的故事题材,以及时间推进的制约,无法在正面完全展开爱情的铺陈描写。”孙甘露笑言,“当然爱情也是非常美好的事物,但是含蓄点到,欲言又止的描写,也会有不错的效果。”
《千里江山图》从未出现过“爱情”。“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爱情却在这个关于信仰的故事里得到升华。
写作关乎内心,阅读让人与人贴近
年轻时是邮递员,走遍上海的大街小巷,孙甘露认为成为作家与曾经的职业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写作是相当内心化的,不同的人在一个具体的环境里面,他所感受到的、他所领会的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常年居住在上海的人,未必会注意到上海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每一个不同季节下雨,雨水老建筑上渐渐收干的那种感觉。“写作的人关心的就是这个东西,把气候变化、日光风雨带给人的感受特质抓住,如果没有的话,那上海对你来说也就是一张嘴里面的一口牙。”
孙甘露在写作过程中保持着一种松弛的状态,“先锋派”的归类、外界评价、获奖与否,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无碍于心。“我觉得写作就是你对这个事情有兴趣,然后你再去研究它,然后来表现它,这个过程就蛮愉悦的。”

孙甘露不为写作设定计划,也没有具体的计划。近期他广泛阅读材料,“你看材料以后你就沉迷在材料中,觉得材料比这些虚构的小说有意思多了,非常非常精彩。”
对于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和课程,孙甘露认可其在广义上对写作能力的一种训练,“创意写作只是引导的方式,写作确实也需要一点训练,但是也需要一点点天赋,在我看来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在“4·23”世界读书日当天做客复旦,孙甘露认为在当今阅读电子化、购书便利的时代,办书展、读书会仍有不可取代的价值。“传播方式在变化,这个商业的模式在变化,有一条是永远都不会变的,就是人跟人要见面的。作家处理的,无非也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孙甘露策划“思南读书会”,每周六固定举办,已坚持10年,办了450多期,为大众搭建公益的阅读与分享平台。复旦很多老师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如陈尚君、陈引驰、郜元宝、汪涌豪、张怡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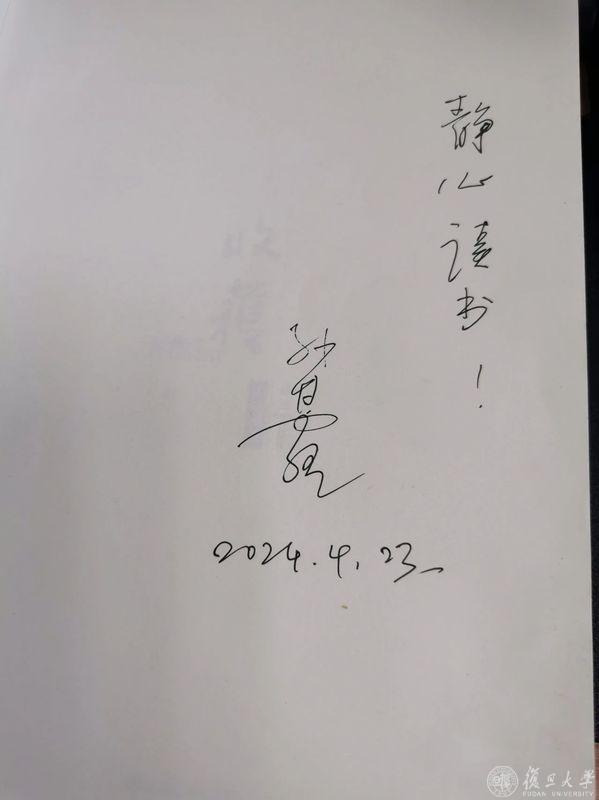
采访结束,他寄语复旦学子:“静心读书”。那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老师对学子的期待。





